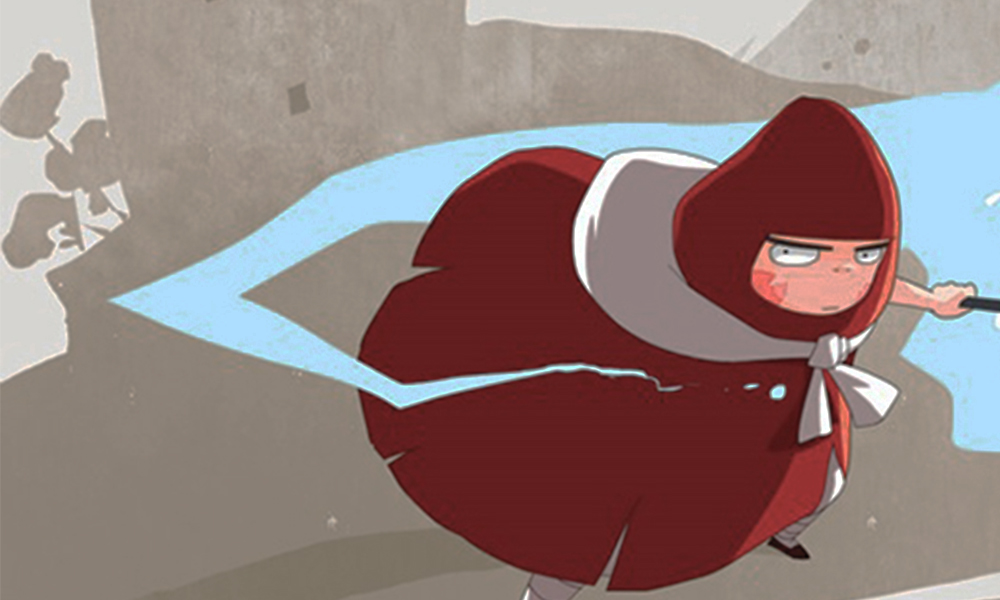30′55″


30′55″
#电影/上海/2013.10.20/6081 次观看
刚刚最后《日和》里, 我的角色是那个腹语师,打娃娃那个。这个小东西是我们当时作为玩乐性质的时候做的。这里边的很多词儿是我们自己顺的。比如说我把里边的觉得不好玩的词就给改掉了,像是女孩松山爱小姐。她原文是“我出道的时候就跟经纪人交往了”。我就把这词改成了“老娘当年就是靠潜规则出道的”。
说说我自己。在接触配音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人民的播音员。在人民广播电台里,在话筒前,宣扬一些什么。后来我就想当然地去报考播音系,然后我就顺理成章地落榜了。
我这个梦想未遂之后呢,其实还没有特别过分的沮丧。因为我对我的失败是有预判的。那个时候,我妈妈从同事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分厂正在招考配音演员。后来特别巧。阿拉东北人,我家就在长春,所以我就骑了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长影。
我也不知道去了该干嘛。到了那儿,工作人员跟我说:“你肯定要准备些什么片段、段落什么的,要让老师来考察你啊”。我什么也没有拿。这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就给我的一个住在长影附近的一个学妹打电话。她正在搬家,很多东西都打包了,只有课本还在外面,就给我拿了一本高中语文书。
我那时候也饥不择食,没有办法,拿着语文书我就进了考场。其他同学都是脱稿的,都是诗朗诵啊什么。“啊! 黄河!”都特别棒。我哆里哆嗦拿着一本语文书,随便这么一翻,翻了一篇课文,鲁迅先生的《药》,就念了一段《药》。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出席面试的这些老师是出于何种考量就把我给选上了。反正,我时至今日非常感谢鲁迅先生的《药》。
那时候长影,从建国初期一直到八十年代,大家一定觉得很熟悉。很多老电影里都有这个厂标,那个时候觉得是一个艺术圣地。它的辉煌就好像9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一样。当时有一些人为了能够考长影,他们去翻墙。翻墙进去,结果墙上是有电网的,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触电身亡了。
我到长影的时候大约是1995年,那时候自己也觉得挺骄傲的。当时我们的厂长是金毅女士,她是在《罗马假日》当中配赫本的。然后她安排了一个老师给我们进行一些培训,专业培训。台词课啊、表演课这些。这个培训大约持续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培训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她也想留下一些人。我那个时候呢,社会闲散人员,所以上课出勤率很高。而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是有的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情,他们的表现没有我好。所以我的业务不是最好的,但是最终是把我暂时地留下了。我就做了一个长影译制厂的一个临时工,官称叫「合同制演员」。
在长影其实也参与了一些片子。但是基本上都属于,我们管那叫「群杂」。群杂中的群杂,你们可以理解-就是龙套中的龙套。这是后来我在网上发现的,当年的一个老的字幕表,上面有我的名字。为什么我这名字前面没有一个对应的角色名字?什么汤姆啊什么,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整个儿这一块属于其他配音演员下边,所以我是根本没有对应的角色。
在长影阶段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那个时候是一个起步阶段,觉得自己挺差的。首先就是对口型,对口型是配音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口型这个东西呢,尤其是译制片,你要去追它的节奏,赶它的强拍。你每句话都要追上,如果追不上的话那口型就过去了,那这场戏就录得失败了。
比如说人家一个“哦”,你肯定不能来一个“哦”。或者说比如韩国戏。人家女孩说:“欧巴﹋”,然后你如果来一个特别淡定的“大哥”,这肯定就觉得特别跳。
我对这个为什么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到北京之后,我是东北人,不太适应北京的干燥。我到了北京之后嘴就裂了好多口子,特别疼。那时候遇到了一个角色。这角色忽然有一场戏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忽然就开始笑起来。
我配到这儿,本身刚到北京的时候也不是特自信,很胆怯。然后这时候就笑了。 但是嘴痛啊,就“嚯嚯嚯嚯…”当场不出意外地被配音导演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怎么笑的, 啊? 人家什么样,你什么样”。我说那就哈哈大笑吧。“哈哈哈哈”笑完之后就在那儿等着。“导演, 能不能通过啊? 能不能通过?”一看导演, “嗯”, 点点头,可以过了。啊,这颗心算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然后低头一看台词本,上面有一滴血,我这个嘴唇,但是当时也不觉得什么。
这是译制片。译制片当中你必须得去追很多他们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国产戏就觉得特别好对呢? 这口型特好对呢? 不是。外国片子你就赶它的强拍,他张大嘴的时候你也稍微大一点儿。但是国产片很多字都要对上,每一个字都要对上。这是一个难题。更加难题的难题呢就是,最终要你配的那个台词跟演员本身说的那个台词是两回事儿,没有什么关系。这当中有很多很多原因。此处只能省去了,因为也没什么好说的。
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剧中人,他要朗诵一首诗。比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首诗。这演员他背不下来,他就数数。数数, 他怎么数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他这样数。七言诗,你对吧。这怎么办? 没有办法呀! 开始吧, 马上。“远上寒山石径斜,白 云 生 处 有 人 家,停车 坐爱 枫林晚”。
当时觉得这个,因为我的天资不够聪颖,所以那时候真的对口型就是我的天敌。这道坎儿我过了好久都没有过去。在长影的时候,后来有一个记者跟我聊天, 说:“你是不是在长影阶段就已经崭露头角了?”我说:“我少露马脚就不错了”。
时间来到1997年。那个时候忽然之间长影译制厂变得特别特别的不景气。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事情做,大家都没有事情做。然后我去问别人,人家说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来了,我也不知道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联系。
这时候有一个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说:“你啊,最好想想清楚。配音是一个夕阳产业,而且以你的声音条件,你一辈子都配不上主角儿了”。我特别感谢这位老师,因为难得在彼时彼地有这样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心里话告诉我。我思考了很久,也跟家人商量,然后我就离开了长影。
97年中秋节,我21岁,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还是在配音这个圈子里混迹,因为实在是别无所能,甚至可以说百无一能。混得也不太好。但是自己的业务确实比在长影阶段有了一些进步,逐渐我获得了一些稍微重要一点的角色。
到了99年的时候,美国人通过试音把我选上了。因为当时是《泰坦尼克号》的正版影碟版引进到中国,然后把我选上了为里边的杰克配音。杰克! 当时特别激动,但是激动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我特别想把这个角色配好,但是说实在的,我配得实在是不怎么样。后来每次人家提到我或者介绍我的时候,都拿这片子说事儿。其实我心里特别的纠结,特别的汗颜。
因为确实在我那样的年纪能配到这样的角色,是一种侥幸,是一种荣幸。但是你配得不好就变成了一种不幸。因为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少年英才特别难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演宝黛,不是所有人都能演斯嘉丽,你在合适的时候碰到了合适的东西,但是你没有把它处理好,这就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后来前两年《泰坦尼克号》又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它又来了一遍,以3D的形式,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去配这个角色了。杰克获得这个船票只有一次机会,我也是。
其实可能生命中、生活中很多东西在某种层次上就是得而复失的。就好像是王家卫的电影一样,永远都是擦身而过。
在那之后,我就特别特别更加珍惜这类的机会。我先后配了《指环王》中的Frodo、还有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中的梁思成、还有就是《变形金刚》。我配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对自己还稍微比以前要满意得多了。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技术在进步,但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应变能力还没有跟上这个进步。这可能是一种异化。
以前我最早在电影厂的时候,我们做一部片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走进那个录音棚,录音棚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放电影的小型的电影院。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上面有专门的放映员给你放映,外面有专业的录音师给你录音,用磁片录音。那时候那感觉很好。一个银幕整个是为你呈现的,然后你对着话筒配里面的喜怒哀乐,那种感觉特别神圣。
现在呢进入两千年以来,基本上画面都被抓取到数字音频工作站当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对着电视机、对着显示器、顶多对着一个投影机来配的,这种感觉其实就不像以前了。这是技术上。
另外一点从这流程上。我们最早在长影的时候,一部片子来了,首先翻译翻好剧本,跟导演交流,把台词校译好,按照口型校译好,然后所有的演职人员大家一起开会,大家来肯词-肯定台词。
这个过程是创作氛围特别浓的一个过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确定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大家才进棚配音。那种感觉很好。更早的时候,等到那个解放初期的时候,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配音艺术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一部片子来了,首先大家集体看片,看片之后开会讨论,从政治上、从思想上、从艺术上等等角度来分析这个片子。然后每个人再去试,到试好这周期要维持很久。试好角色之后,有的还甚至要写自己角色的心理分析报告。然后最最重场的一些戏,他们甚至要真人把这场戏演一遍。然后最终他们才进棚录音,进棚录音的时候如果谁还没有把台词背下来,导演当场就摔本儿,那简直就是无地自容的一种感觉。
但现在我们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很多片子讲究全球同步上映,同步上映什么概念呢? 《变形金刚3》的时候,我来到棚里跟配音导演见面。配音导演廖菁老师,她说:“小姜,你觉得你配这个角色你大约需要多久啊?”我说:“如果给我三天时间的话,我会把他配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要三天呢? 因为刚才大家也看到这个角色一直在喊。“大黄蜂!@#%&…”,都是这样的,特别疯狂。一个人很难永远保持自己声音最好的状态。如果说我喊喊忽然觉得我的嗓子状态不好了,劈了,那可能就得休息,就得恢复状态。恢复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睡觉。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导演对我笑了笑,苦笑一声,说:“所有的人才只有三天的时间”。然后后来这部戏我就用了六个小时,《变三》是用了六个小时配完的。基本是什么状态呢? 喊“ 哎, 擎天柱我在这儿”,一会儿哑了,哑了, 好, 喝口水。杯子一放下就算休息结束,然后这样把这部片子就给配下来了。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进电影院的时候,更多的会选择那些以字幕片形式呈现的译制片,而不会去选择配音的。是这样吧? 而且我相信今天的观众,一席的观众比较特别,相信你们自己很多没有字幕也照样能看得懂。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挺好。观众有他自己选择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作为一个从业者,我只能说当一种创作貌似要沦为一种制作的时候,有些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人无所谓,为所欲为。所以这些年我配的译制片其实在逐年减少。
我也知道在座的很多人一定非常怀念80年代很多经典的译制片,什么《哈姆雷特》、《简爱》这些东西。我也特别欣赏这些老艺术家。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些配音作品,我觉得他们配音的这些东西,确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这样的。
现在有些人在学,但是学的都是怎么样的?“哦~是吗~”,“哦~天哪~”。他学的这些东西它是没有根基的,都是皮毛。它只有外壳没有灵魂。因为那个时候国外人家的表演就是非常诗意的,人家配出来很诗意的是非常正确的。它是有根基的、有感情脉络、有它的创作思路可循的。
现在很多人光学那个外表不行,因为整个世界电影的发展潮流在变。你去看看一分钟之内《哈姆雷特》、《简爱》这些片子它有多少个镜头,你再看《变形金刚》有多少个镜头,它现在更多的是描述一种状态。
但有的人就会说:“那为什么不能用那个时候那种配音的状态来完成现在的片子呢?”就觉得现在的配音不好听。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电影潮流在变,演员已经不那么演了。
配音讲求什么呢? 讲求还魂,就用中文的形式把它的一切东西还回去。如果人家演的都是状态,“哦,是嘛?”“大黄蜂”,人家是这样的,如果你还特别优雅的那样,放在上面肯定是不贴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事儿。
这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词叫生不逢时。我也特别憧憬那样一个美好时代。如果一个配音演员赶上那个时代,我总觉得是一件特美好的事情。但我现在放眼望去,我所配的片子,大家也看到,都是这些。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劝自己,我说,也许我所处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有一种假设,这种假设你不能否定它,就是你所认为的那个美好时代当中的那些美好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美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让这个时代变得美好。
说了半天,你说现时代的配音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越是身在其中,我越难以总结这些东西。尤其是我在准备这次一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可能很多东西我拎不出来,因为我太在当中了。
我有的时候看书,看到佛家讲‘不立文字’,我不知道佛陀当年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以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语言和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但是有的时候文字并不如语言那般丰富、丰满和对机。它表现的东西不一样。而且就语言本身来说,语言本身能传达的东西,它也是不可言表的,是难以言表的。
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两个大爷的例子。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是想说明这件事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收集起来,然后应对到我的角色当中,应对到我的戏当中,然后让你觉得恰到好处。
我先讲第一个大爷。有一天我在北京要赶到一个录音棚去。那天我坐公共汽车到了一站下车之后呢,发现时间来不及了,我必须换出租车。但是换出租车的话这条路会非常堵,而且特别绕,要绕一大圈。
但我知道这边肯定有胡同是可以穿过去的,我就选择我赌一把吧,从这边步行过去。两面都是围墙,没有什么人。我越走越不自信,天很热,我也很躁,时间也快到了,就觉得前面怎么对不对啊,是不是走错了。
这个时候迎面过来一大爷,扇着扇子过来了。我想碰见人了赶紧问一下吧,我就迎上去,台词是这样的:“大爷,请问公园后门怎么走?”他说:“一直往前, 左转就到了。”大约是这样。“谢谢大爷”,台词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一场戏的话,我们配音会怎么配呢?“你好大爷,请问公园后门怎么走啊”?“哦,你呀一直往前,然后左转就到了”。可能就是差不多这类的感觉,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合理的,在此之前我觉得很合理。
但这大爷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大爷,请问那个公园的后门怎么走?”“你呀,就、就从这儿过去,一直……一直走走走走”,我说,“行行行行,大爷你别说了”。你不知道生活中有这样的可能性,它特别的真实,它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个大爷,说说第二个大爷的事儿。最近几年的国产电影我比较推崇《风声》。虽然我也参与其中,我也参与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真心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学习。
这当中呢有一场戏令我刻骨铭心。后来前几年我去给某演艺公司的一些新进的艺人做台词培训,我当时在他们的课上我也讲到过这些戏。
我说,“大家看过这个戏吗?”有的人说看过,有的人说没看过。然后我就简单地把这剧情给他们描述了一下:黄晓明饰演的人阴谋败露,跟张司令决定让王志文来做一个替死鬼、替罪羊。所以从背后张司令就向王志文举起了枪,就这样一场戏。
台词是什么呢? 王志文的台词是这样的:“我操你大爷! 我操你大爷!”然后他回头把张司令推到墙边,扼着他的喉咙,前面那句话之后他就把视线转向黄晓明,说:“武田长,我对你,你是知道的”,就这样一场戏。
我把这情境跟这些艺人交代完之后,我说你们来,就用台词来演这场戏。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操你大爷! 我操你大爷!武田长!我对你!你是知道的!”大概这样。
我说我们…他说,你说这表演有误吗? 我觉得他是这意思,没错。我说你去看王志文他是怎么演的。他一把把张司令推到墙边,“我操你大爷! 我操你大爷! 武田长,我对你,你是知道的”,这样的。
那一瞬间真的把我震撼了。惟其胸中有泪,是以言中有物。就这样的老演员,他想到的这种东西跟我们常规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会说配音演员干嘛的,就是学人说话的嘛。你是不是会很多种声音啊,你特别会变声。
以前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好像能变声特别牛,我既能配这个又能配那个。你看我刚才那些角色,没有一个重样的。但是现在如果说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种创作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从外部的,就是他的表情、肌肉、他的口型开合大小、他的眼神、从他的肢体动势去着手;
另一方面就是要从他的心去着手。言为心声,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生的功课。语言当中能展现一个人的东西极为丰富。你从他的话语当中你可以听出他的出身、背景、教育经历、成长环境,一切的一切。甚至你从语言当中,你能听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
以前余光中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贾宝玉不可能对林黛玉说,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其实你从这个话当中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于一个语言当中能够听出一个人的思路。思路是什么意思?
我前一阵子有一天在家发呆,坐在沙发上什么也没做,手机就在手边,忽然电话响了。是一个骚扰电话,推销楼盘的。有一个特疲惫的年轻人。我说,“喂?”他说“你好先生,我们这边有个楼盘刚刚开盘,你有兴趣在北京置业吗?”就这样一个电话。
如果平时的话可能我就十动然拒了。但是那天我也是发疯,我抽风,无聊嘛!“先生您有兴趣在北京置业吗?”“在哪儿啊?”然后对方:“对不起先生,打扰了”,哐,挂了。
你从这话语当中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经历了多少次坎坷多少次拒绝。所以其实生活中你如果多想的话,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平时我自己总结,我告诫自己的,在从事这个行业当中也好,做人也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师古不泥,善用其心。
我觉得很多老的东西我们要学,但是不能拘泥,而且要善于用自己的心灵。这个「善」字有很多种解释,我觉得每一种解释都能符合我的意思。
近些年我从事一些配音导演的工作,电影啊、动画电影啊、包括一些更多的是国产电视剧啊,我是出任配音导演,对于配音导演的要求其实更加宏观。就是说你必须体察到这整个作品中的所有的细节。然后你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具体到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台词、每一个气息当中。
这是我们当时配动画电影《魁拔》的一个场景。站着挥手的人是动画导演王川,后面坐的是王大锤。他给我分的角色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想配个帅一点儿的,但是导演希望我配这个,他是树国的一个店老板。
其实情节是什么样的:一父一子来到这个客店,他们拿了一个假的文耀,就相当于假的身份证要住店,但是没有真正的文耀你是住不了店的。所以我当时配得非常势利,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很势利的。“像这样的天气里,睡在大街上也别有一番情趣”。
导演说,不对。然后我们两个开始探讨。他说,这个人他是服务性行业,你就让他彬彬有礼很得体就好了,但是不要让他带有一些鄙视或者是势利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不想传达。
其实这个精神给我的震撼非常之大。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但是却使我非常震撼。就比如说前几天我还碰到一古装戏,古装戏很常规的一个场景。朝廷要斩人,士兵开道,群众围观。忽然上来一个家属,这个罪犯的家属来拦驾说:“哎呀! 相公啊! 相公!”然后士兵说:“让开! 让开!”就这样一场戏。
配这个士兵的是我的一些学员,我现在带的一些学员,他们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让开让开!”后来我就跟我的这些学员交流,我说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传达了什么。
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把我们很多通过我们能传达的一些锋利的东西、一些暴戾的东西要少一点儿。我说,这个士兵他只是执行任务,他的表演上看不出任何凶恶的成分,你不要下意识地就把他配得那么凶,你只要很简单的“让开让开”,就OK了。你不要“让开让开!”凶神恶煞一样。
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因为配音是一种从属的创作,人家演员演好了之后我们是follow人家的表演,然后我们所改善的东西不多。其实从这一点一滴,我希望从我们的口中传达出来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正一点儿的能量。
但是这个学员为什么会这么配呢?他会觉得这个戏特别「满」。“让开让开!”而且他在此之前看到的很多作品当中,也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这个「满」所谓我们行话叫「戏足」,戏给得足。这个配音跟做人一样,做人做得太足了。失真,反倒没人相信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恰到好处就好。配音是一个挺枯燥的工作,你说它有意思也很有意思。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简单机械地重复一些很枯燥的东西。但是就像做人一样。做人其实特别孤独,而且特别单一、单调。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在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自己。可能我在家的时候是个儿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配音的,然后走到街上可能就是一路人,但是终归都是你自己。
我觉得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我能体验到不同的生命个体。因为只要你进了棚,你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是。你可能一会儿是王子,一会儿是乞丐,一会儿是强奸犯,一会儿是什么柔弱的什么什么人,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它非常的丰富。你在棚里有的时候会特别疯狂。
这就是配《魁拔》的时候当时一个照片,就特别疯狂。你完全投入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把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就忘却了配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说我在配音的时候,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物种当中,体验各种生命个体的各种喜怒哀乐。通过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乐与怒啊、喜或愁啊,然后学习珍视自己手中的小小幸福。
我乐在其中。
配音演员、配音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