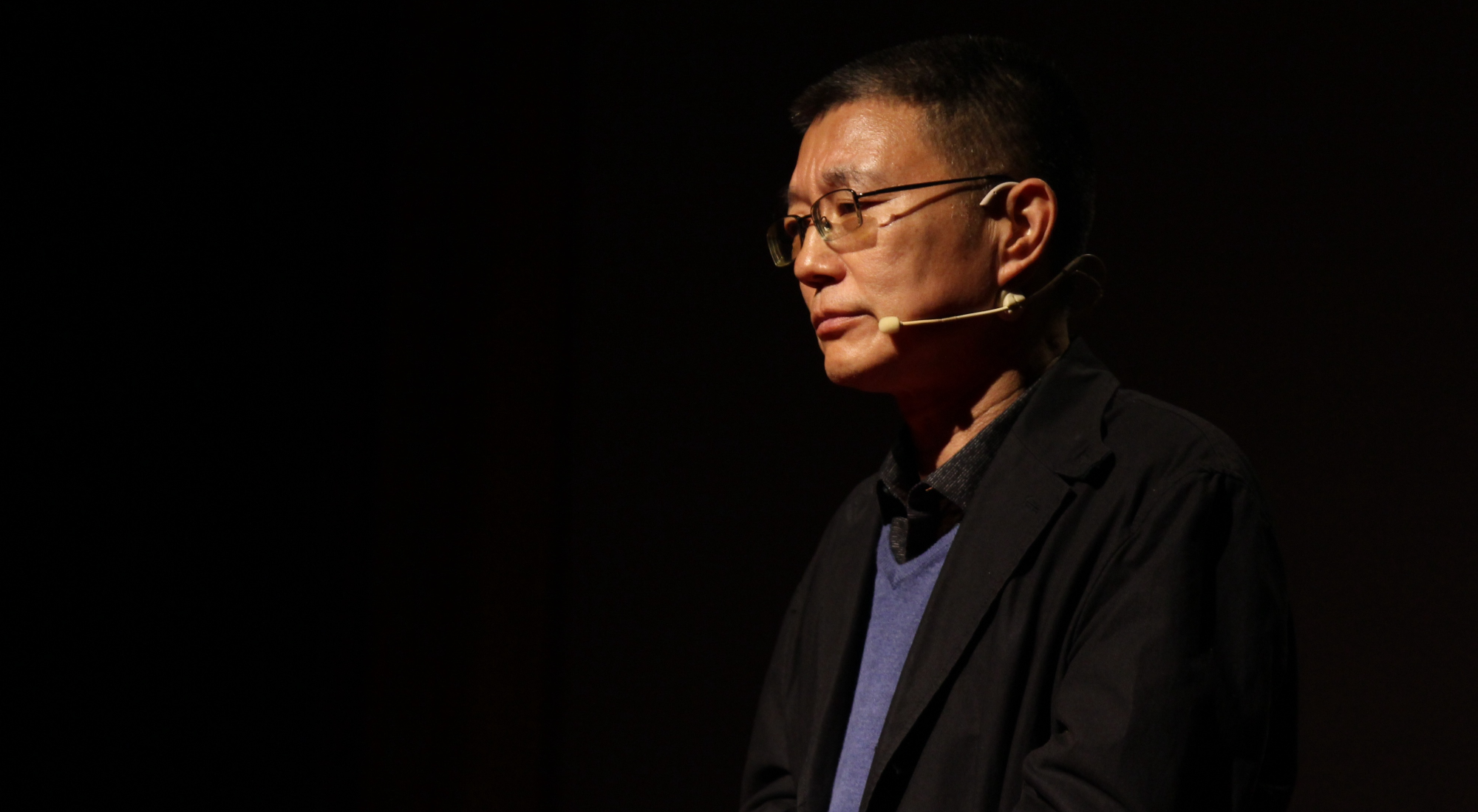38′46″


38′46″
#艺术/上海/2021.12.12/26109 次观看
我是宋欣欣,我从小跳舞,现在编舞,是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老师,也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联合艺术家。
我小时候跳舞是因为开心,进了专业舞蹈学校之后是为了得到认可,再后来学编舞是想表达自己的感受。而现在我几乎不上台了,因为当众跳舞这件事情不再让我感到快乐。
艺术不是竞技体育
在舞蹈这个行业里,从小就得面对各式各样的评判,高了矮了胖了瘦了,跳得够不够高,转得够不够多,笑得够不够好看。

1996年,我11岁,考进了一所专业的舞蹈学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最前面的正中间,因为只有站C位才说明你跳得好,你被认可、受重视,而站不到C位的时候是需要难过、需要落泪的。
当时的中国舞蹈还处于比赛为大的时代,所有专业舞蹈院校像选拔奥运会选手一样地选拔一个叫“桃李杯”舞蹈比赛的选手。那个时候的我当然也想成为一颗“桃李”,去比赛、去与人竞争、去赢。
那些日子,就好像有两只手竖在我的眼睛旁边,这个“桃李杯”就是小小的我能看到的唯一一条窄窄的路,似乎只有参加比赛拿了奖才能得到老师的尊重,并拥有光明的前途。

▲ 2000年“桃李杯”时的宋欣欣
这真是好大的一个误解,艺术不是竞技体育,真实世界对艺术的要求要复杂得多,一次标准化的胜利真的意味不了什么。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当我候场的时候,总觉得地面是倾斜带刺的;而当我在场上的时候,总觉得黑漆漆的观众席射来的是冷冷的光。
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当了七年舞蹈演员。有一次上一堂现代舞课,那个老师进教室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来,大家找一个自己觉得安全和舒服的位置站好。”当时我的眼泪“唰”就掉下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一种舞的价值不是为了站C位。我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自己觉得安全和舒服的位置跳舞,而起舞的理由可以不是为了被看见或者被认可。那是一种松绑式的理解,让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瞬间。
2010年,我考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学现代舞和编舞,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位老师,其中一位叫王玫,她在实践中第一个告诉我,美不是只有一个样子,舞蹈里的人味儿比舞蹈重要。
2012年之后,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国内专业的舞蹈比赛开始慢慢减少,针对青年舞蹈创作者的各种扶持计划开始出现,比如说有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培青计划”,还有国家艺术基金的“青年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的“青孵计划”等等。

我是幸运的,在恰好的时间被这些计划培养过几次,通过几个中型的作品,慢慢开始了独立实践的过程。
之后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并没什么编舞的才华,而创作这件事好像也没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充盈。
我不得不开始琢磨,到底人为什么要跳舞?我们为什么要去发明和执行一些看上去完全没有实用功能的动作呢?舞蹈的理由真的只是为了塑造和展示一个尽善尽美的身体吗?
《悠悠视界》
很快,我有了一次探索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些人,我们共同创作了一个作品,它叫《悠悠视界》。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来了,全国的剧场全线关闭。2月,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制作出品了一档线上的舞蹈教育节目。
一个男孩的回课视频吸引了剧场团队的视线,他叫悠悠,当时11岁,来自武汉,妈妈是一位医务人员。
(请前往演讲视频观看)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间和地点,被隔离在家的悠悠就这样每天编舞、跳舞、画画。悠悠的处境可想而知,但他抱之以舞的积极行动,自然松驰的编创,还有满墙的涂鸦,打动了剧场团队。
2020年5月剧场团队找到我,我们决定找一些不同的人来共同创作一个作品,让大家用各自的舞来诚实地诉说自己的生命体验。
2020年8月剧场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发布了一则非职业舞者的招募启示,收到了143份报名视频,看到了143位舞蹈着的人和他们对舞蹈的不同理解。
(请前往演讲视频观看)
他们对舞蹈的理解,是我在职业舞者群体里很少听到的。职业舞者群体里好像很少再有关于什么是舞蹈或者为什么跳舞这类问题的讨论,所以当看到、听到那么多不一样的、生动的解释的时候,我真的被打动了。
从看到这些视频开始我就想,一定要把大家都放到作品里,在征求同意之后,我们就以视频的形式把他们放到了演出的最开头。
但是一个剧场作品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其中的13位舞者。
最终因为距离的原因,悠悠并没有参加到这个作品的创作中来,但因为他是这个项目的点灯人,所以我们仍然把这个作品定名为《悠悠视界》。
这13位舞者每一位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扮演任何人,每个人都参与创作,是自己的动作设计。
我没有去改造他们的身体,或者把他们训练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本身是由他的经历塑造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选择尊重他们本来的样子。
每一个段落我们都是从沟通开始的,然后在大量的即兴和练习中,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身心特点,直到属于他们的舞蹈方式和剧场形式浮现在我们眼前。
66岁的项晴是作品里年纪最大的舞者,她是个画家,却坚称自己是个“画画的”。

生于1954年的她,经历过那个时代所经历过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知青下乡,还有辞职创业等等,但时代的波折没有使她的生命萎缩,反而使她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逆行者。
在儿子回答她可以独立时,她毅然关闭公司,开始旅行。我认为,她应该是在那个信仰被不断颠覆和反转的时代,活出了自我的人。
作为一个66岁、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要站上舞台是需要勇气的,而对“画画的”项晴来说,这不过是又一场旅行。
项晴的舞是新疆风味的,跟她的人一样,很飒很自在。我想她潜意识里之所以会选择这种节奏鲜明的舞,正是因为这种舞跟她的生命体验存在着某种贴合。
而正是因为这种特质,我把她和同样自信又松弛的王煜颖放在了一起。

王煜颖生于2012年,没有专门学过舞蹈,本来是陪哥哥来面试的,结果看其他孩子跳舞的时候按捺不住来摸了一下我,说“姐姐,我也想跳”。然后就披着一头大长卷发,毫不怯生地即兴跳完了一整支忧伤的音乐。
好像对于小朋友来说,跳舞这件事情就不用学,他们真的天生就会。和项晴不一样,王煜颖的舞是Waacking(甩手舞)风味的,但是跟项晴一样,也是同样飒,同样自在。
她们两个人先在作品里面聊了聊关于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话题,然后就面对面地坐着开始跳舞。

两个同样性别,但年龄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舞者,通过不同的舞蹈所呈现的既是两个自在生命的对话,也是时间两端的对话。
一个是传统风味的自成一格,一个是当代流行风味的自成一格。一边是日月沧桑过后的从容,一边是生命刚刚开始的好奇。一面是不同时代的身体记忆,一面是可以不被改变的、自在的生命力量。
对于27岁的蒋梦莹、31岁的吴佳婧,还有25岁的叶艺清来说,舞蹈是生活的平衡物。

科研的压力让蒋梦莹很痛苦,在我们排练的一年多里,她认识的和她身边的朋友有一位自杀,三位退学。2020年考核过后,她也经历过一场情绪上的崩溃。
心理医生让她平时要多专注在自己的呼吸还有肢体的动作上,她也觉得好像跳舞可以暂时地让那些不开心的情绪从身体里面流走,我们就给她编了一段只有呼吸的舞蹈。
在梦莹的这个段落里没有音乐、没有背景,她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观众还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就是她跳舞时呼吸的声音。

但是她就觉得她不能全都放在工作上,她的心也不能全都放在亲人身上,她需要有一块自己的地盘。

她每个周末克服三地奔波的困难来上海参加排练,就是觉得生活需要一个暂停键。
排练开始不久,她母亲便离世了。
我们在她的舞段里使用了一张齐肩高的白纸,让她用身体把这张白纸反复弄皱再捋平,然后站在上面跟她妈妈的生前影像一起打了一段八段锦,最后把这张白纸叠成花束,放在一个凳子里,升向空中。

佳婧说这段舞,是寄给妈妈的一封信,她想让妈妈知道,她现在可以了,她会好好地活成一个流动的自我。
对吗,佳婧?

叶艺清在疫情过后放弃广州安逸稳定的生活,离开曾经对她家暴又难以割舍的男友,一个人来到上海,狼狈地为自己创造着新的生活。
叶艺清的舞是Jazz(爵士)、Waacking(甩手舞)和Hip-hop(嘻哈)等这种当代最流行最飒的舞。我想她选择的背后既是时代审美的折射,也是个人生命质感的体现。
在叶艺清的这段舞里,我们用她的旁白替代了音乐,看她在现实的自述里用强烈的爆发力撕扯、甩头,把一个年轻女人茂盛的生命能量从头发尖上喷了出来。
(请前往演讲视频观看)
可能青春的真相并不美,所以她们三人的生命状态和项晴、王煜颖是截然不同的,有一种在牙根指缝的疼痛感。
尽管生命经验是痛苦的,但她们的舞蹈经验却依然能有一种把这些痛苦洗掉的力量。她们让我认识到,舞蹈本质上是一个积极的行动。
如果一个人很低落,但他仍然想要跳舞,说明总是有一丝积极的能量在起作用,或者至少是一种向往积极的愿望。当这种内在愿望燃烧并转化为身体愿望的时候,舞蹈就发生了。
王佳妮,王姝欢,王思佳和胡宏俊是四位有职业舞蹈背景的舞者。与上述三位姑娘借舞蹈治愈生活不同,他们的疼痛感大多来自舞蹈带来的外界评判。

王佳妮和王姝欢都是零零后,是舞蹈编导专业大三的学生,都是那种可以在排练厅从早上八点待到晚上十二点的努力姑娘,跳舞的时候竭尽全力到有一种想要挣脱肉身的感觉。
王思佳生于1984年,国家一级演员,生完孩子之后离开了舞台。她从小是在古典主义审美的熏陶下长大的,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即使她现在剪短发、穿潮服,但她的舞蹈仍然追求那种保守的、理想的、逼近永恒的美,不允许露怯,不可以乱来,也不能够失败。目前的她正在面对从一个优秀的舞者到导演的身份转型和心理落差。
生于1980年的胡宏俊是街舞圈的元老,现在在努力推动文艺舞台上的街舞发展。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所以他的舞跟我们平时在电视上常看见的那种竞技性街舞不太一样,少了进攻性,但多了戏剧性。
对于前面的那些舞者来说,舞蹈是现实生活的出口,是他们做梦的地方;但对于我们这些职业舞蹈人来讲,舞蹈就是现实生活,它是事业、是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跟舞蹈的关系就没有那么轻松。

但其实前后对比着来想一想,舞蹈跟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的,比如梦莹的科研和在座各位的工作是一样的,它们本身是中性的,它们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生命跟这些活动的关系。想要活得好,就不能让它凌驾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生于2011年的王钦瑀是王煜颖的哥哥,他街舞跳得很好,在报名视频里说自己是那种可以独自在家练习八小时的孩子。

两兄妹住在哈尔滨,排练的中后期,基本上就是由爸爸妈妈带着从哈尔滨飞来上海排练。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疫情一直反复,所以他们很辛苦。演出结束之后,他妈妈说:“宝贝们,人生经历就是爸爸妈妈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
许汪容平生于2009年,是那种不爱搭理人,不爱看着人说话的男孩,但是只要你碰到了他的点,他就可以一秒变戏精。

他的业余时间排满了各种活动,但他最喜欢跳街舞,因为“跳街舞又酷又好玩儿还可以交朋友”。
但他也特别容易厌倦,排练的时候,只要他厌倦了,就赖在地上不起来,所以我就叫他“许大爷”。
一开始我还要求三个小朋友要跟大人一样专注,但后来我发现,与其让他们被动营业式地表演专注,还不如放他们自由。
孩子的世界当然不只有玩乐,但他们最开心的就是玩乐,所以我们就暂时地让舞台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请前往演讲视频观看)
我发现小朋友都特别容易厌倦,在排练的时候就逼得我要不断地给他们换新花招,否则他们就不开心。像这段舞,还有这段音乐,其实两个小男孩早就跳烦了,但是等到正儿八经演出的时候,有了观众,有了掌声,他们就又来劲了。
三个小朋友当然还是小朋友,但因为我们排练的时间比较长,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一直跟大人共同经历着,一年多下来就基本处成了战友关系,大人跟小朋友之间直呼姓名,有事没人瞒着,不耐烦了就相互嚷嚷。
演出结束后,许汪容平的妈妈就跟我说,其实许汪从小就是一个在社交方面有点困难的孩子,是舞蹈让他开始跟同龄人自然相处,而《悠悠视界》让他开始跟人自然相处,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一个有社交困难的孩子了。
心 中 的 大 好 河 山
| 潘文佳 |
潘文佳生于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是一个程序员,在上海租了一间小屋,没有谈过恋爱,喜欢剧场,喜欢艺术,我们叫她潘潘。

潘潘在报名视频里跳了一支踢踏舞,唱了一首《出塞曲》,那真的是一首很美的歌。
我想潘潘的心里应该有一团火,否则她不会选择在日复一日的编程工作之余,去跳这样一种小众的,但是充满了节奏和力量的舞。
她心里面也应该还有一种柔软而广阔的力量,否则她不会选择去唱这样一首看尽山河的歌。
潘潘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当其他人在排练厅经常性地情绪翻涌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在排练厅的角落里面,安静到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对她的忽视。
那个时候我就想,等到潘潘站上舞台的时候,我们要用好多好多的手电筒,一盏一盏地把她打到最亮。
2021年1月17日,在我们第一次完成片段连排之后的一周,潘潘就因为公交车祸离世了。

遗体告别仪式上,潘爸爸跟我说,他以前不支持潘潘干学习和工作以外的事情,所以潘潘来参加我们的排练也没有告诉他。但这回他要来看演出,他想知道潘潘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尽管最终潘潘没有能够像我现在这样,站在舞台上接受爸爸和观众们的注目,但我想影像里她唱的歌、跳的舞,以及她生前舞友们在舞台上替她踏出的节奏,至少勾勒出了她心中的山河。
新闻可以冷漠,但艺术必须有温度,通过舞蹈和剧场这个载体,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事故新闻中的“女乘客”心中的大好河山。
(请前往演讲视频观看)
我第一次在报名视频里面看着潘潘这样扬着头、背着手,跟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确定她一定要存在在这个作品里面,跳一支踢踏舞,唱一首《出塞曲》。
尽管她离世了,但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变过。
杜鹃生于1982年,是一个重度暴食症患者,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瘦到只有25公斤,瘦到让人不忍直视。
其实她的报名视频准备得很仓促,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在她强烈的要求之下,我们还是请她来到了现场。
见面之前我担心她的外形会让作品有卖惨的嫌疑,但是等看到她的现场和她的那个世界之后,我知道她是一部作品千载难逢的人选。

艺术感觉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杜鹃就是那种可以进入到自己幻想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人。她其实没有怎么学过舞,她的身体也不允许她再怎么去跳舞,但是她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在灯光下、在音乐中,幻想出一个世界,然后用她有限的身体力量在里面流浪。
杜鹃想要美,就是那种古典主义的逼近永恒的美,无论是身体上、面容上,还是灵魂上。但残酷的是,现实中的杜鹃所拥有的艺术力量,恰恰来自她备受摧残的身体、面容,还有灵魂。
当她得知最后所有人上台只会穿自己平时的衣服的时候,她特别失望。她来跟我说:“欣欣,我不喜欢我现实中的样子,我也不喜欢我平时的那些衣服,我想要站在舞台上被打扮成一个公主的模样。”
其实杜鹃的外形,她对现实杜鹃的憎恶和对理想杜鹃的向往,会使得她在舞台上不管做什么都很有力量。可惜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透这一点,我就想要尊重她的理想。
所以当看到王思佳跟她的双人舞即兴发生的时候,我便决定要让她在托举当中去尽情地伸展身体,然后腾空着去接近“理想杜鹃”的那种美。

同时把她坎坷身世中消极的部分,比如被亲生父母遗弃、患上暴食症等以时间轴的方式放到了她舞段的开头。
然后再把她生命中积极的部分,比如说第一次恋爱、第一份工作、女儿出生等以同样的方式放到她段落的结束,试图以阅读生命的两种方式,去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杜鹃。








▲ 滑动查看更多
2021年1月30日,第一次观众探班的舞台上,杜鹃受到了特别大的关注,因为她的身体和经历实在太特殊了。
当时她特别开心,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希望大家五月份到剧场来看她。结果二月份的时候,她在家里不小心摔到了头,三月份她便离世了。
杜鹃自己说,过去她不愿意出门,因为太瘦了总会有人指指点点。而两个月的舞蹈学习让她不再惧怕路人的眼光,所以一看到我们的招募帖子,她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她想让她的生命中多一些积极的因素。
第一阶段排练的时候,杜鹃基本上没有缺过席。当她被关注,尤其是在她单人段落排练的时候,她的身体里面会灌满那种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并因此闪闪发光。

但集体段落排练的时候,她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总能感觉到她在偷瞄我有没有看她。
那个时候我不懂她眼睛里的信息,但现在想来,她有多了解自己的奄奄一息,应该就有多贪恋在跳舞得到关注时自己身体里那份不费力气的勃勃生机。
所以她看我其实是在确定我有没有在关注她,她不想偷懒,但没有人关注她的时候她就是没有力气。她不想暴食,但她真的控制不住。她想要改变,想要对抗,想要爱,但大多数时候她真的没有力气。
我想,舞蹈对于杜鹃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被关注和重新创造自己的机会。
至今为止还有两个属于杜鹃的瞬间让我难忘,一是她以极慢的速度把眼睛睁到无限大,二是她以同样慢的速度把胳膊肘弓起,把手掌张到无限开。
尽管这两个形态看上去非善非美,但当一具瘦骨嶙峋的、像玻璃一样脆弱的身体内部充满了这种向往无限力量的时候,它便拥有了一种大于“美”“善”这类字眼的力量。
可惜她在的时候,我并没有对她身体的原生能量以及那种裹挟着生死的矛盾做更深的探索。遗憾的是,我和作品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面向观众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收到了挺多反馈,有观众说羡慕他们借舞蹈表达自我的坦诚和勇敢,有观众说感觉一部分的“我”起立加入了他们,也有人说接受不了这样的当代艺术。

从2020年10月1日正式的排练开始,到2021年5月21日的首演以及11月14日的封箱演出,在这14个月里,我们这些人一起度过了四季,见证了生死,经历了一个作品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数不胜数的焦虑、脆弱、沮丧、质疑,还有欣喜、倔强、和解和感激……
尽管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困境,但自相矛盾的存在和对生活的爱是共通的。大家放下手中的一切,每个周末到排练厅来跳舞、奔跑、流汗,是把这个作品的完成当作劳动之余的另一种存在,完成的是生而为人的多种可能性。
演出结束了,但属于他们的艺术生命才刚刚开始。

一席的西西在看完我的讲稿之后,她问我,她很好奇大家在走完这一趟之后是什么感觉,于是我就挨个儿地去问了问大家。
哈尔滨的这个小男孩,王钦瑀,他特别认真,给我写了好几页纸,他的总结陈词就是,“干就完了!”

每一位舞者都很用心地给我写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一一地说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自己现在几乎不上台了,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在他人的眼光里享受舞蹈。但《悠悠视界》的舞者让我看到,舞蹈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的是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强度,而人是高于这个载体的存在。
所以他们不怕,他们还能体会到这种身心的愿望,我真的很羡慕。
《悠悠视界》让我确定,身体是创作的材料,它不是创作的目的,而那些附着在身体上的,属于人的信息才是。说到底,舞蹈本身是一件小事,重要的是舞蹈的人。
比艺术的结果更重要的,
是艺术的行动
其实国内外一直有艺术家在实践这样的创作,比如德国舞蹈剧场大师皮娜·鲍什(Pina Bausch),法国艺术家杰罗姆·贝尔(Jerome Bel),还有中国艺术家文慧和小珂×子涵等等。

尽管大家选择的形式,还有针对的命题不同,但我想应该都拥有两个基本的理念:一是传递一个信息——舞蹈不专属于职业的舞蹈精英,它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舞蹈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能够完成的动作,去享受舞蹈带来的愉悦,或完成自我的表达。
二是对世俗定义当中的“舞蹈”和“美”提出质疑。到底什么是舞蹈?只有拥有高超技巧和整齐划一动作的才是舞蹈吗?到底什么是美?只有年轻的、瘦削的,拥有完美比例的身体才是美的吗?
其实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内涵在被不断地更新和拓展。时至今日,只要是定论,都值得被质疑,而这一类作品就是在向那些约定俗成的定义发出质疑。
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剧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是国内唯一一家专门做舞蹈的剧场,他们首部出品制作的是我们这样一种既不宏大也不完美的作品,我想这也表明了一种比过去更加开放的舞蹈态度。
在这个剧场旁边有一个很小的绿地,有些时候我会在那里碰到一个环卫工人,坐在公园的长条凳上用树叶来吹一些不成调的曲子,像鸟叫一样,很好听。
我觉得他比电视上的演奏家更打动人,因为他追求的不是艺术的结果,而是艺术的行动。我非常希望我们实践的也是艺术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艺术的结果。
谢谢大家,谢谢参与到这个作品的每一个人。












《悠悠视界》导演、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教师,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艺术家